從武威醫簡治久咳上氣方「茈胡」談中藥名稱同源分化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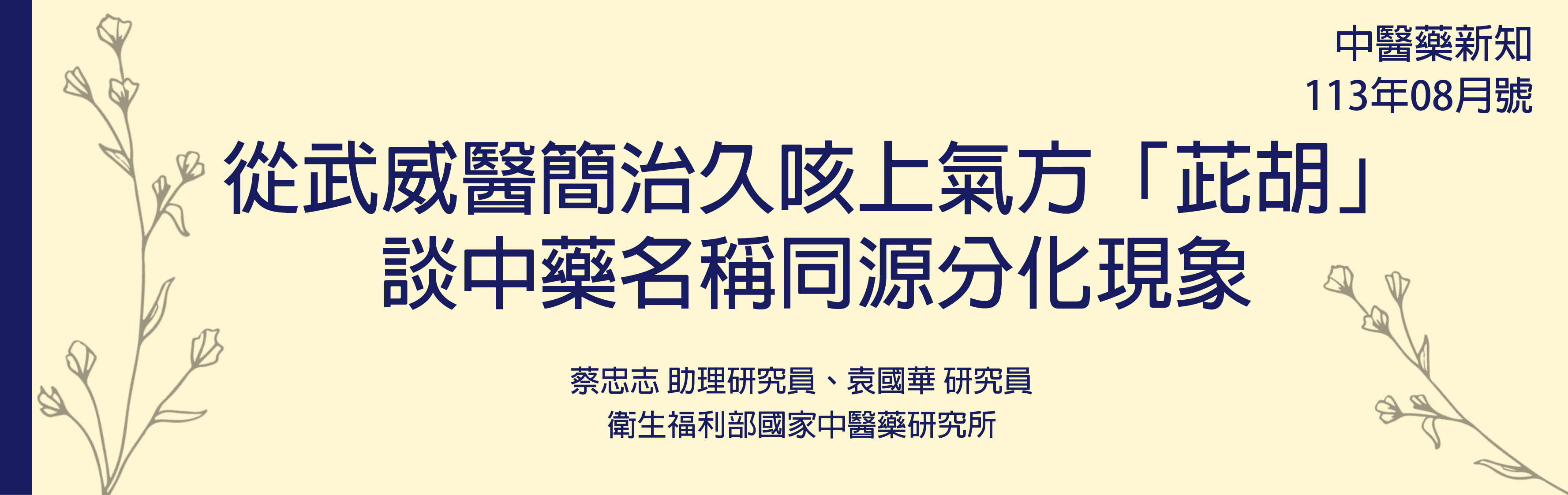
1972年11月,在甘肅省武威市旱灘坡,發現一座出自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 (25〜55) 的東漢墓葬,墓中出土與醫藥相關簡牘92枚,原簡編號3、4、5,為治療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方:
治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卅歲以上方:茈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烏喙、薑各一分,凡六物,冶合和丸以白密,大如嬰桃,晝夜含三丸,消咽其汁,甚良。[1]
相似處方見編號第79,內容如下:
治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卅歲以上方:茈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烏喙、薑各一分,凡六物,皆冶合和丸白密,大如嬰桃,晝夜含三丸,稍咽之,甚良。[2]
其中「茈胡」一藥,在甘肅省博物館與武威縣文化館合編的《武威漢代醫簡.摹本釋文註釋》書中釋讀為「柴胡」,書中並未詳敘理由,但作者曾就宋以前本草及醫方中「茈胡」一詞作過查考,在先秦至兩漢時期,雖有《戰國策》「柴葫」一則例外[3],其他無論諸如漢代小學著作《急就篇》,漢代出土「居延醫簡」等文獻皆作「茈胡」。在六朝至隋唐之間,諸刻本、寫本醫籍中,含茈字藥「茈菀」、「茈草」、「茈藄」……等都改成「紫菀」、「紫草」、「紫藄」……等都作「紫」,再無寫作「茈」者,「茈」字似乎有作為「茈胡」專名的意味。至於「柴胡」用法大約出現在初唐[4],在此之後曾有一段混用的時期,一直到宋代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所收錄的《嘉祐本草》與《圖經本草》已可以很明確的看到視「茈」為古字,並將「茈胡」均校改為「柴胡」。是故,將「武威醫簡」中的「茈胡」釋為「柴胡」可謂言之有據。
此方在漢代《傷寒論》小柴胡湯亦有用治咳症 (辨太陽脈證并治) 者,陶弘景《本經集注》所收載「名醫別錄」載茈胡主「諸痰熱結實」,唐本草亦云「傷寒大小柴胡湯,爲痰氣之要。」然而後世卻少見以柴胡入喘咳痰氣等方,這背後似有值得深入探索之處。
一、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方經驗用藥思維解析
簡文中的主治症候「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與張仲景《金匱要略》所載「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近似,即咳喘上氣遷延日久之意。方中用茈胡、桔梗、蜀椒、桂、烏喙、薑等六味藥,據《神農本草經》蜀椒主治「邪氣咳逆」,牡桂主「上氣咳逆結氣」,烏喙主「咳逆上氣」,乾薑主「胸滿咳逆上氣」。本經中雖然未收錄茈胡與桔梗與咳氣上氣相關的功效,但在《名醫別錄》則記載茈胡主「諸痰熱結實」,略晚的《藥性論》也認為桔梗能「消積聚痰涎,主肺氣氣促嗽逆」。這條處方的六味藥都與咳逆上氣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是一條主要由經驗用藥思維組成的處方。
經過唐宋之際,上述幾個與咳逆上氣有關的中藥在處方中所扮演的定位也有所變化,除了桔梗仍作為止咳要藥外,蜀椒、桂、烏喙、薑多被視為祛風、溫裡、散寒、止痛的用藥,而茈胡則為治寒熱和解表裡、疏肝理氣升陽之用。似此藥物主要作用的變化,牽涉的可能原因很多,就上引《神農本草經》所載內容其實已經透露出一些訊息。
二、中藥名稱所見同源分化現象
桂在本經中有「牡桂」、「箘桂」兩個品項,據本經所載「牡桂」主「上氣咳逆,結氣,喉痺吐吸。利關節,補中益氣。」,「箘桂」主「百病,養精神,和顏色,為諸藥先聘通使。」,依本方的主症應當用「牡桂」。烏喙即烏頭,是毛茛科植物烏頭的地下塊根,母 (主根) 為烏頭,附生者為附子,連生者為側子,細長者為天雄,兩岐者為烏喙,五物同出異名,在本經中佔其三:附子、烏頭、天雄,其中附子治「治風寒,欬逆,邪氣,溫中,金瘡,破癥堅,積聚,血瘕,寒濕痿躄,拘孿,膝痛,不能行步。」烏頭治「治中風,惡風洒洒,出汗,除寒濕痹,欬逆上氣,破積聚,寒熱。」天雄治「治大風,寒濕痹,歷節痛,拘孿緩急,破積聚、邪氣,金瘡,強筋骨,輕身,健行。」依本方的主症當用「烏頭」也就是烏喙,這一點上本方與本經所載吻合。椒,在本經中收有秦椒、蔓椒、蜀椒三個品項,秦椒治「風邪氣,溫中,除寒痹,堅齒,長髮,明目。」,蔓椒治「風寒濕痹歷節疼,除四肢厥氣,膝痛。」,蜀椒治「瘧,及欬逆,寒熱,腹中癥堅,痞結,積聚,邪氣,蠱毒。鬼疰。」依本方的主症當用「蜀椒」,這一點上本方與本經所載吻合。換言之,武威醫簡的收方年代與《神農本草經》的成書年代不但相近,在使用藥物的想法上有吻合的地方,兩者之間應該存在著一定的聯繫。
「牡桂、箘桂」、「附子、烏頭、天雄」、「秦椒、蔓椒、蜀椒」[5],三組藥物各自之間既有藥材基原植物,藥用部位,也有藥材產地等關係[6],這是古代博物學直觀記述下的典型現象。並且從兩漢到唐代之間的本草記述,可以觀察到隨著使用經驗的累積,對於藥材基原植物型態的觀察,同一基原植物不同產地藥材的療效、不同藥用部位的功效更趨於細緻,隨之同源藥物的品項也產生分化的現象[7],其主治症狀與功效的描述亦有移易的現象。根據這個視角,「茈胡」應該有深入檢視的必要。
三、「茈胡」分化為「柴胡」與「前胡」兩藥名現象分析
「牡桂、箘桂」、「秦椒、蔓椒、蜀椒」在上古時期就存在「桂」、「椒」等統名,由此分化而出的藥材品項脈絡相對清晰,相較之下「茈胡」的分化就比較隱晦一些。
陶弘景在《本經集注》在「茈胡」與「前胡」條下的兩段文字頗值得重新審視,他在前胡條下說:「前胡似茈胡而柔軟,為療殆欲同。而《神農本草經》上品有茈胡而無此,晚來醫乃用之,亦有畏惡,明畏惡,非盡出《神農本草經》也。」,又在茈胡條下說「今出近道,狀如前胡而強。」從陶弘景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線索:其一,在本經的年代裡並無「前胡」這個藥物,「前胡」這個藥物是在陶弘景的相近年代才出現的新藥名或新藥物;其二,「茈胡」與「前胡」兩個藥長得非常相似,差別只在於「前胡」較為柔軟;其三,這兩個藥物的療效差不多雷同。按照古代博物學的規則,這兩味藥物的淵源應該與桂及椒的情況相當近似,在更早的年代裡,極有可能被視為同一種藥物。這一個推論在陶弘景相近年代醫家的著作中,是可以找到佐證的,而且前輩學者章太炎也早就留意到這個現象,他說道:
本草本無前胡,《別錄》有焉,……按此知柴胡、前胡本是一類,土宜小異,呼聲漸殊,《秘要》、《崔氏》小柴胡湯,直作小前胡湯,其證也。[8]
章氏所謂「《秘要》、《崔氏》小柴胡湯」,實即唐.王燾《外台秘要》卷一引《崔氏方》「小前胡湯」,其原文如下:
又小前胡湯,療傷寒六七日不解,寒熱往來,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寒疝腹痛方。胡洽云出張仲景
前胡八兩 半夏半升洗 生薑五兩 黃芩 人參 甘草炙各三兩 大棗十一枚擘
右七味切,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四服,忌羊肉、餳、海藻、菘菜。古今錄驗同[9]
《崔氏方》 (《崔氏纂要方》) 是隋唐之際醫家崔知悌所著。這條條文的主治症候除了「寒疝腹痛」之外,其餘都是張仲景《傷寒論》少陽病的提綱證,其組方及分兩也與同書所引述仲景小柴胡湯完全相同,而且從「胡洽云出張仲景」一句,直指胡洽所引用收錄的張仲景方就叫「小前胡湯」。胡洽即南朝劉宋醫家胡道洽,著有《胡洽百病方》,主治下的小字注所指可能就是《胡洽百病方》。從這條條文可以說明,六朝到隋唐時期的醫家,至少有胡洽、崔氏及唐.甄立言《古今錄驗方》等三家,認同前胡與茈胡可以互相替用,甚至有可能這三家認為前胡跟茈胡並無差別。此外,在日本現存最早醫書《醫心方》卷十〈治七疝方第三〉引東晉《范汪方》茈胡之下也加了「一方前胡」的註解。
綜合來看,茈胡與前胡的代用在唐以前並非特例。這些六朝到隋唐之間醫家處方所留下的線索,大大增加了前胡是從茈胡分化而出同源藥物的可能性,特別是從陶弘景「名醫別錄」以下本草諸家無不強調其下氣、散痰實等主治效用。進一步推論,原本茈胡主「諸痰熱結實」的效用,應該是被移易到前胡之下,而保留茈胡正統之名的柴胡之所以在後是少見於喘嗽之方的緣由也呼之欲出了。
結語
武威醫簡自1972年出土以來,以其與張仲景傷寒方思路略似,頗有作為互證的參考價值,備受臨床醫學及文獻醫史學家的關注。然而若依目前所使用的柴胡 (柴胡 (北柴胡) (Bupleurum Chinensis DC) 和狹葉柴胡 (南柴胡) (Bupleurum scorznerifolium Willd)) 套用在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方之中,實有枘鑿不入,令人難以索解之處。本文透過唐以前本草文獻的梳理,發現古代本草中存在者同源藥物的分化現象,並據此尋找到柴胡與前胡由茈胡分化而出的歷史脈絡,若此推論得以成立,武威醫簡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方的「茈胡」,應該對應現今的前胡,不但符合較歷史事實,亦符合臨床運用的原理。
參考文獻與註解
[1]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1995年。
[2]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2,1995年。
[3]《戰國策.齊策三》載:「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 ((漢)高誘注、(清)黃丕烈札記,《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卷10》,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頁6,1803年。) 案:1972年在馬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中並不見這段內容,傳世《戰國策》又經北宋曾鞏校補,已失原始傳本的樣貌,故已不足為證漢代已存在「茈胡」之外的用法。
[4]《急就篇》:「黃芩伏苓礜茈胡」顏師古注云:「茈,古柴字。」顏師古是唐初人,據此最晚在唐初,茈胡、柴胡就已經開始互用。
[5] 在日本平安時期《延喜式》中,甚至將三者都歸類為山椒 (中村亞希子、神野惠,〈古代の山椒〉,《平成25年度 山崎香辛料財団研究助成 成果報告書》,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機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頁23-29,2014年。) 。
[6] 西漢初期 (168B.C.) 馬王堆漢墓出土《五十二病方》載有「桂」、「美桂」及「囷 (菌) 桂」等三種桂名。成書於東漢的《神農本草經》則見牡桂與箘桂兩種。陶弘景說:「《本經》惟有箘、牡二桂,而用大同小異。今俗用便有三種,以半卷多脂者單名桂,入藥最多。」,至唐代《新修本草》,牡桂與箘桂不僅產地不同,植物型態也不一致,而桂則是各種桂的統稱。秦椒與蜀椒都作為花椒使用,兩者之間是產地的不同的關係。
[7] 同源分化字、詞是指有「源出」與「衍生變化」關係的文字、詞匯。參王寧,《訓詁學原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頁51-53,1996年。
[8] 章太炎,〈論治溫用藥之妄〉,《章太炎全集.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213,1988年。
[9] (唐)王燾,《外臺秘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頁72,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