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疫啟示錄—蘇東坡與聖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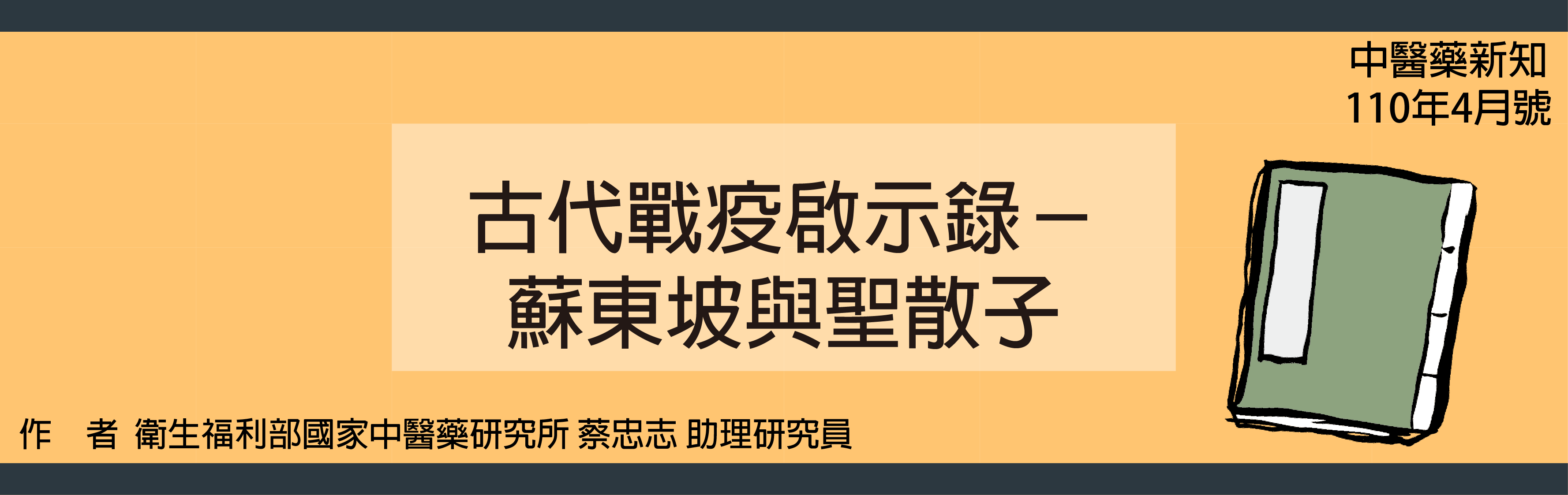
~ 聖散子是一道處方,是一部方書,也是環繞傳統中國千年抗疫史的一則公案~
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 年)七月,蘇軾(東坡)生涯史上第三次蒞湖州主政,到任後進〈湖州謝上表〉,文中提到「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句中以「其」自稱,說自己不「生事」,暗諷朝中「新進」人物(政治新貴)「生事」(意指變法)。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上表,以「悛終不悔,其惡已著」等四大罪名彈劾,欲置之於死地,最後蘇軾入御史臺入獄受審,僥倖宋神宗網開一面,將蘇軾謫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就是所謂的「烏臺詩案」。「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涯的一大轉折,但也開啟了他和歷史上抗疫名方「聖散子」結下不解之緣。
一、聖散子與名醫龐安常
「聖散子」名傳千古,與當時傷寒大家龐安常(安時)有極大的關係。
《東坡全集》卷三十四收有〈聖散子方敘〉和〈聖散子方後敘〉,在〈聖散子方敘〉中,蘇軾對「聖散子」方的來源交代得很清楚,他說道這條處方是他苦苦從同鄉人曹谷之處求來,當時還指著江水,對曹氏發誓密不傳人。他謫居黃州期間,正逢時疫流行,他自己也經歷過染病,服聖散子治癒的過程,並將此方合成藥散施諸百姓,藥驗卓著「所活不可勝數」。
蘇軾以聖散子方抗疫不僅止於黃州,數年後神宗元佑四年(1089 年),杭州地區禍不單行,大旱災之後跟隨著饑荒,饑荒之後又爆發了嚴重疫情。蘇軾自請赴杭,獲准以「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事」。有了六年前在黃州抗疫的成功經驗在前,他仍利用「聖散子」治疫疾。他的策略是自籌財源以官府統籌辦理賑濟抗疫事宜,租用寬大房舍為病坊,取名「安樂坊」,配備了官吏、郎中,又請來楞嚴院裏的出家眾,按「聖散子」方採購藥材,架起大鍋煎藥,給前來患者分發一人一碗,當場喝下。據《聖散子敘》載,「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再服別的藥合併治療);至於症輕的,喝過一二服,即『心額微汗,止爾無恙』。」蘇軾這次的防疫顯然也是成功的,他在〈聖散子方後敘〉中寫道:「去年春(1090 年),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
蘇軾原本對於曹氏秘聖散子方的作法,打從心中是不贊同的。有了兩次抗疫成功的經驗之後,他不惜悔誓,將此方授予當代人稱蘄水醫王的龐安常,希望藉由龐安常的醫名、醫著讓聖散子方與曹谷之名流傳不巧。證諸歷史蘇軾的期待確實實現了,但是也惹出了不少麻煩。稍晚於蘇軾的文學大家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憶及聖散子從風行一時到消寂的歷程,他說﹕「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蘇軾同鄉)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前世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蘇軾是在元豐三年至七年(1079 - 1083 年)之間任職黃州,宣和年間是(1119 - 1125 年),從蘇軾出聖散方到盛行於京師地方,前後歷經 40 年,其原因可能就是如葉夢得所言,聖散子因為附於龐安常《傷寒總病論》之後,連傷寒大家醫王龐安常都不敢有所非議,因此聖散子也隨著《傷寒總病論》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 年)刊刻行世,才得以廣為人知,而此時蘇軾與龐安常都已相繼謝世十餘年了。
二、聖散子文本的流傳與聖散子方
聖散子方是一道處方,但也是一本專書;《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館藏中醫線裝書目》就著錄有:「《聖散子方》一卷,北宋述古堂舊本」,2005 年該書還曾經由中醫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這本書原為醫史文獻學家范行准先生收藏,其後轉贈予中國中科院圖書館。據學者考證,這部書為明人郭五常付梓於鄖陽(今湖北鄖陽區),除了收錄有聖散子方之外,還附刊華陀病危十方、經驗三方,中科院藏本則還收有治療痞疾、臁瘡等續錄 28 方。從原本的單一方,初刻時增錄為 14 方,後續擁有者在復刻時又增錄為 42 方,以形制而言,這是一種備急方,也可能是一種善書,更可能身兼兩種作用。蘇軾在杭州主持防疫事宜時就曾命人抄錄貼於通街大衢,明代弘治癸丑年的那一場瘟疫,吳邑令也曾「以其方刊行」,其用意不言可喻。
聖散子最早是以單方的形式收錄在《傷寒總病論.時行寒疫論》,其原方內容計 22 味藥,聖散子與同篇所收錄的方最大不同點,是龐安常並未加註此方的主治症狀。這點可能是與方後附有蘇軾方序,已清楚明白的提到:「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瘥,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小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是為一種藥性微溫的傷寒病的通治方,龐安常雖未曾加註主治功效,然而將之編錄於「寒疫」之下,立場其實也已表明的非常明白了。
近代有學者分析此方的組成,說道:「方以麻黃、細辛、附子、吳茱萸、高良薑溫陽散寒,以蒼朮、厚朴、藿香、半夏、石菖蒲、草豆蔻燥濕,以茯苓、猪苓、澤瀉滲濕,白朮健脾化濕,防風、藁本、獨活以風勝濕; 柴胡、枳殼、芍藥、甘草合爲四逆散,調暢氣機之用。以方測證,不難看出此方是爲寒濕之邪而設。」;另 1987 年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傷寒總病論〉釋評》一書,對聖散子方,特別加註按語》:「從方藥組成看,全方偏溫,用於時行寒疫病自無不可,但若云:『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未免言過其實。』」既然古今醫家對聖散子藥性及適用症並無太大歧異,那麼又何來公案之說呢?
三、不問證候如何,無不愈?
「不問證候如何,無不愈?」世間真有如此靈效醫方?後代醫者論及這一段歷史,多以蘇軾不通醫學,一筆帶過;然而,龐安常呢?當代傷寒大家,難道只為了顧及他與蘇軾的交情,而能任意草菅人命?其實這是低估了當時的時代風土對文人、對庶民,乃至對醫家的制約影響力。
宋代歷朝皇帝多雅好醫方,這是宋代歷史的一大特色。舉宋太宗趙炅為例,在他執政的第 3 年,便「召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竟蒐羅了驗方「萬餘首」,這就是醫方鉅著——《太平聖惠方》的前身。在他晚年還下詔創辦了御藥院,院中並整理出了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宮廷內的成方製劑規範——《御藥院方》(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這類成藥處方配本,在宋代中期之後也拓展到惠民政策的一環——熟藥所與《和劑局方》,在《和劑局方》頒行地方各處之後,民眾得以不用尋醫,可以按方買藥,在醫療資源不充裕的年代或偏鄉,大幅度提高民眾的自救能力。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就曾評論說:「《和劑局方》之爲書也,可以驗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制,尋贖見成之丸散,病痛即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謂至矣。」但是問題也出在同一地方,過去「臨病制方」的醫師守則,一變而為「一方通治諸病」(朱震亨《局方發揮》)的弊端。
第一版《局方》發行的時間點 1078 年,正是蘇軾任職黃州期間,可想而知,蘇軾在論及聖散子方時說「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正是這個時代風氣的表現。
四、宋明之際疫病的鑑別無非採時空作為標幟
由於傳染病、流行病除了相染、暴卒之類的特徵之外,初起的體徵:惡寒、發熱都是相通的,在很長的一段歷史裡,傷寒、天行、溫病、溫疫等稱呼都用來混稱傳染病和流行病,晉.陳延之《小品方》中就說道:「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爾,不說病之異同也。」基本上在宋以前的疾病分類,烈性或急性傳染病,都歸屬於傷寒病之下,也統稱外感病。外感病的病因、論治,在宋代以後有了極大的進展,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就是龐安常。龐安常曾提出傷寒與溫病應該分治,他認為熱症較明顯的溫熱病是由異氣所致,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可以說是數百年後溫病學的前驅。
不過從龐安常到明末第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溫疫專論著作《溫疫論》(1642 年)問世之前的六百餘年間,論治疫病仍以傳統六淫之說佔勝場。以六淫之說來解析疫病的特徵,無非是利用疫病流行相關時、空條件的觀察,希望能使疫病的治療更加準確。
南宋初醫家陳無擇在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說:「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往往頃時,寒疫流行,其藥偶中。抑未知方土有所偏宜,未可考也。」此處所說的「方土」很明顯是區域性的地理因素,明代醫家王肯堂講得更清楚:「昔坡翁謫居黃州時,其地瀕江,多卑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濕而病,或因雨水浸滛而得,所以服此藥而多效。是以通行於世,遺禍於無窮也」。
寒疫看似是一種病性的用語,實則不然;明代醫家吳綬為寒疫定義為:「乃天之暴寒為病也。凡四時之中。天令或有暴風寒之作。人感之而即病者。名曰寒疫。」換言之,寒疫是四時異常氣候「暴寒折人」(《傷寒蘊要全書》)所致的外感病,是一種暫時偶發的流行病,仍然不脫是一種時令相關的疾病。
五、以五運六氣理論為聖散子重新定義
清代溫病大家吳鞠通曾對歷史上「寒疫」一詞作過觀察,並加以定義,他說:「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狀,則憎寒壯熱,頭痛骨節煩疼,雖發熱而不甚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相類,若役使者然,非若溫病之不甚頭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蓋六氣寒水司天在泉,或五運寒水太過之歲,或六氣中,加臨之客氣為寒水,不論四時,或有是證,其未化熱而惡寒之時,則用辛溫解飢,既化熱之後,如風溫證者,則用辛涼清熱,無二理也。」溫病學在清代中葉成熟,吳鞠通論述「寒疫」的這段文字,摻入論治外感病的兩種新醫學元素;其一是依病性,而不依病因來論治外感病;其二是借用五運六氣的推算法則分析疫疾的病性。
聖散子方在明代還有大規模使用的紀錄,但是效果仍不理想;明醫家俞弁《續醫說.聖散子方》中,曾紀錄了明代弘治癸丑年,吳地中疫癘流行「吳邑令孫磐,令醫人修合聖散子遍施街衢,幷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無一生」。在此之後疫病當分寒溫陰陽之別逐漸為世醫所認同,聖散子隨之在歷史的舞臺逐漸消寂。但仍不失為醫家喜歡探究的熱門標的,只是推論的理論基礎一轉為五運六氣理論。
張鳳逵在《增訂葉評傷暑全書》一書,明確地指出;寒疫多病於「金水不斂」之年(古代運氣醫學的用語),聖散子寒疫挾濕之方而設,永嘉、宣和年間服此方殞命者,是因爲以寒疫之方,誤施於溫疫而致。清乾嘉年間的名醫王丙,運用「大司天」(360 年為一個大司天週期,六年為一司天週期)理論,分析聖散子方在宋代治療疫病前後迥異的效果,認爲蘇東坡以聖散子治疫時,正值第六十三甲子(從黃帝甲子算起)太陰濕土在泉,而至宋徽宗辛未年時,已交六十四甲子,相火已開始用事。運氣環境變了,而仍以溫燥的聖散子治疫,難免會有貽誤。陸懋修承其外曾祖之學,在其著作《世補齋醫書文.十六卷》中,再一次重申:「公(蘇軾)謫居黃州,尚在六十三甲子,濕土運中,方必大效。至五十歲後,又值六十四甲子,相火之運,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聖散子方的歷史走到清代以司天理論解析,基本上已是窮途末路,在醫家眼裡,只能算是一種聊作談資的歷史文本了。
六、結語
聖散子方流行近千年歷史,因出於蘇軾之手,盛極一時;又因殺人無數而不得不湮沒於歷史的洪流。它的對應主治,大抵上在南宋初年陳無擇筆下,就已經被定調為「寒疫」類的處方,這點歷史上的醫家似乎無人提出疑義。究其緣由,可能是與龐安常在《傷寒總病論》中就將之歸類於「時行寒疫論」之下有關。
既然早在龐安常手中就已經將聖散子方定調,那麼又何以從昔日活人無數的濟世良方,跌宕成「殺人無數」的利器。這一段醫學史的喧然大波,又該如何評價呢?有人將矛頭指向了蘇軾,認為是蘇軾對疫疾本質的認識不清所致。若然,蘇軾生涯中曾平息黃州、杭州兩場疫疾風暴,純然是運氣好?那麼據《雍正江西通志》記載,元豐三年至七年(1080 – 1084 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在任監筠州鹽酒稅期間也遇到了一場瘟疫,此時的蘇轍也采用了聖散子藥方,「遍謁病家與之」、「醫活者甚衆」,又該作何解?
清代醫家又從大週期的五運六氣理論,試圖為聖散子在蘇軾手中有效,在他人手中無效的歷史現象解套。證諸現代研究,七至九世纪是冷凉期,十至十四世紀是温暖期,十五至十九世纪又進入寒冷期。蘇軾使用聖散子方的兩次時間點都落在第十世紀末,屬不適合使用聖散子的溫暖期;而明代弘治癸丑年吳地的疫情,又進入十五世紀適合使用聖散子的寒冷期。因此大司天理論的推論,似乎並不精確。
蘇軾固然以「一切不問」的武斷方式,搭配他的名人效應來傳播聖散子,招致後人對他與聖散子的種種負面評價。然而,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此,聖散子的不當應用才是事實。在溫病溫疫理論成熟之前的探索期,以功過苛責蘇軾,苛責吳邑令孫磐等人都有失公允。究其實,在聖散子流傳的歷史,所有牽扯到的相關人物,都不過是在他們身處的時空背景下,作出他們覺得最正確的抉擇罷了!
參考文獻
[1] 張家鳳(2001)。「疾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病觀。臺大歷史學報,27,37-80。
[2] 牛亞華(2008)。《聖散子方》考。文獻,2,114-119。
[3] 李健祥(2009)。儒醫平議。中華醫史雜誌,39(5),282-287。
[4] 張立平(2013)。中醫運氣學說與聖散子方的涅槃,世界中醫藥,8(1),99-101。
[5] 余瀛鰲(2018)。蘇東坡與聖散子方。中國中醫藥報,8版。
[6] 小高修司、楊文秸、張再良(2018)。從蘇軾看宋代的醫學與養生—從古代的氣候史、疫病史思考《傷寒論》的校訂,中醫文獻雜誌,2,61-66。

